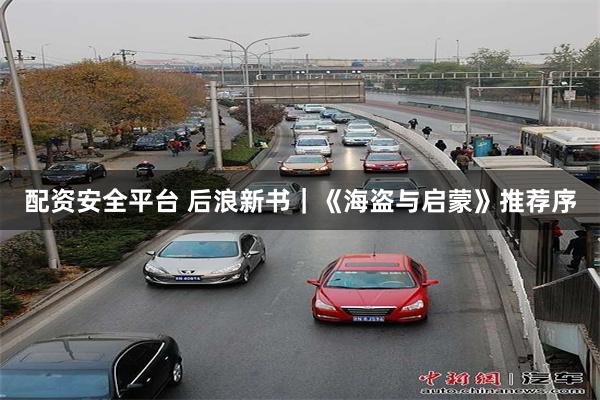
提到海盗配资安全平台,你或许会想到《加勒比海盗》的电影场景,冒险、劫掠、朗姆酒。但在大卫·格雷伯的笔下,海盗不仅是浪漫传奇的主角,他们还可能是自由和平等的实验者。不妨先从推荐序,走进这本神奇的书。
从“世界”到马达加斯加
袁长庚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毫不夸张地说,大卫·格雷伯可能是过去十年间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西方人类学家。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他们所熟悉的格雷伯是那个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我们是 99%”的抗争领袖,或是撰文批判“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笔锋辛辣的专栏评论家。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格雷伯的大量人类学著作都还没有译介至中文世界,中国读者也不清楚这位学者在其自身专业领域的成就和贡献。
展开剩余93%1996 年,格雷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 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类学理论家之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他的博士研究,聚焦于马达加斯加中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动荡、暴力及殖民历史的深远影响。终其一生,格雷伯的思考和写作都与这座地处印度洋西部的“世界第四大岛”密不可分。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马达加斯加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除了偶尔因为旅游目的地推介而出现在航空公司机舱杂志内页,大多数时候它都没有跻身国际新闻的资格。但是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马达加斯加的意义却绝对不容小觑。原因无他:过往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类学家连续不断地在此展开田野调查,名家名作辈出,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学领域内必读文本。
马达加斯加之所以吸引人类学家的注意,原因之一可能与这个群岛国家在西方殖民体系发展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公元 10 世纪,阿拉伯人在岛屿西北沿岸建立了贸易据点,留下有关该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1500 年,欧洲人的船队抵达马达加斯加,并在此建立定居点。到17世纪晚期,法国人在东海岸建立贸易据点,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马达加斯加是横跨大洋的奴隶贸易路线上重要的据点。各种势力在此汇聚,使其成为全球史的一个缩影。格雷伯在《海盗与启蒙》当中描写的很多传说和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进一步说,人类学家对马达加斯加的兴趣,一方面是 20 世纪西方人类学“非洲研究”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重视该地历史脉络复杂多元的文化图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马达加斯加人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各种文化要素的回响和共振。例如,格雷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殖民暴力的历史遗存,以及这种遗存如何造成了当代马达加斯加社会的裂痕和分歧。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大量借鉴后殖民思想(Postcolonialism),将各个曾经被经典人类学视为“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族群还原到殖民扩张的近代史脉络当中,正视其与外部殖民力量的遭遇和冲突。有关马达加斯加的人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活力。
据目前有据可查的材料显示,格雷伯的第一篇人类学作品发表于 1995 年。和大多数人类学青年学者的发展轨迹一样,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格雷伯的成果主要是围绕自己在博士期间收集的田野材料进行专题分析。但稍有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似乎就不满足于将马达加斯加的故事视为人类学理论的注脚。相反,他很早就有意识地探索如何将微观社区中的经验与更广阔的议题联结起来。
例如,一般说来,在美国学术界,刚刚开启学术生涯的年轻人类学者都会把最初的几年花在对自己博士论文的打磨、修改和出版上。一个人类学家的第一本书常常是自己博士论文的修订版。但是格雷伯在出版自己的论文之前,已经写完了三部专著,除了那本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小册子之外,其余两部分别是《迈向人类学的价值理论:我们的梦中假象》 (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Palgrave 出版社,2001 年)、《论可能性:等级制、反叛和欲望》(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 ,AK 出版社, 2007 年)。前者直接对话马克思和莫斯 ( Marcel Maus s ),力图重新思考人类“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 这种能力与形塑社会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系列学术作品的合集,其中广泛讨论了各种概念议题。这些作品虽然都不是民族志写作,但是马达加斯加的影子始终浮现其中。
由此可见,对于格雷伯而言,马达加斯加不是一个作者可以随时返回、翻检论证材料的“仓库”。马达加斯加的地方经验 始终都有超越时空限制、回应一般性议题的潜能。或者也可以说,格雷伯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上人类学家和自己“田野调查地”的关系。在格雷伯的论证体系中,马达加斯加更具“世界性”,而他所处的欧美社会,虽号称当代世界中心,但却充满偏见和幻象。格雷伯的意图从来不止于在西方学术界的宴席上为马达加斯加谋一个位置,相反,他激进地把外部世界带进马达加斯加的框架,以一种有悖于常规论证的策略重新思考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据格雷伯本人在前言当中的交代,《海盗与启蒙》的写作缘 起于他自己收藏的一份由法国人撰写的手稿的影印件。影印件 藏于大英博物馆,内容关于加勒比海盗在马达加斯加的活动状 况。格雷伯取得这份材料之前,就已经在田野调查当中得知海 盗曾经在这座岛屿上长期扎根,但却并未能就这一问题深入讨论。田野调查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间,格雷伯仍然继续留心收集 与马达加斯加海盗活动有关的材料。这本书原本是他和导师萨 林斯合著的《论国王》(On Kings)中的一部分,但因为篇幅过长,索性单独抽出来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
总的说来,《海盗与启蒙》是一份有些怪异的文本。用格雷 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份深受人类学观点影响的历史学著作,但我想哪怕是一个历史学的高年级本科生,也能在其中挑出不 少史料或解读方面的“漏洞”。在这本书里,格雷伯百无禁忌似 的在史实和推论之间来回切换,其目的与其说是坐实某种结论,不如说是打开某种想象空间。这让我想起“占领华尔街”运动 期间另一个流行的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在格雷伯邀请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里,主角是出没于大洋 风浪间、过着刀头舔血日子的亡命之徒(海盗),他们通过和陆 地定居点附近的原住民女性结婚,缔造了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 平等而开放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绝对权威,社会事务的落实 大都仰仗各类小型民间团体的灵活决策。即便有一位“国王”, 他也无权插手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看似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 力中心,但整个社会因为末梢神经的灵活而充满生机。这种生 命力使得马达加斯加东海岸一度成为洲际海上贸易理想的中转 枢纽。大批货物(尤其是海盗通过劫掠获得的巨额财富)在此流通,很多在旧大陆社会秩序中没有落脚之地的边缘人在此聚 集。与人们在小说里设想的推崇丛林法则式的荒蛮大陆不同, 在这里,拳头和刀剑很快就会让位于演说。比起由绝对强力奠 定的短暂优势,人们更相信通过不断协商形成的契约秩序。在 这片沿着险峻高原地形展开的狭窄平原上,人群被复杂的地理 条件精密切割,从来没有谁能够一统天下,但区域内累积的财 富和军事力量一度令人惊叹。
事情还不止于此,格雷伯进一步演绎历史。他认为,这个由海盗缔造的松散政体,为了进一步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曾经向欧洲派遣大量说客和代表。这些人足迹遍布欧洲各大都市,结交权贵,在街头巷尾通过高谈阔论传播自己的思想。于是,一个大胆而又合理的想象是:如果我们的历史都承认轰轰烈烈 的启蒙运动源自学者对当时社会思潮、社会观念的总结提炼,那么有理由想象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就是听了海盗集团派遣的代表在咖啡馆里的高谈阔论之后,才受到了刺激和启发。
如果这样说尚且无法传递此种观点的“耸动”,请诸位读者朋友此刻自行在脑海中将您熟悉的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的肖像,替换为约翰尼 · 德普(美国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男主演)!
《海盗与启蒙》像是一篇精彩的侦探小说,作者凭借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蛛丝马迹,结合人类学意味浓重的推理分析,最终得出了使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过分透露文本中推理和想象的细节,无疑会大煞风景。所以有关这个另类世界的具体展开,我留给各位读者自行探索。在此,我还想补充几点,以便帮助大家更好地走进格雷伯将要带大家观赏的这出发生在三百年前的历史大戏。
格雷伯出生于一个“革命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肯尼斯 ·格雷伯曾经远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母亲鲁丝 ·鲁宾斯坦曾经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的活跃分子。格雷伯成长于纽约曼哈顿岛西 侧的切尔西,这里是“各种激进政治的温床”。格雷伯曾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 7 岁开始就参加抗议活动,16 岁读高中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是大卫 · 格雷伯最喜欢的一个身份,但是 在中文语境中,这个词多数时候都被用作贬义。无政府主义虽 然同样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盟友,却始 终难以摆脱“无组织、无纪律”的恶名,难堪大任。其实,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仇视所有权力机关,更不会期待混乱,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关注秩序问题,只不过他们不相信集中制管理,更推崇根植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自发秩序、自发组织。
由此可以想见,无政府主义和人类学之间的衔接点就是对日常经验的推崇,对自下而上自发秩序形成的赞许。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海盗与启蒙》视为一曲对马达加斯加无政府主义实践的赞歌,其基调依然带有浓重的民族志意味。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小册子中,格雷伯就详细阐述过他对“秩序”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他所依赖的主要论据,就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材料。
在格雷伯看来,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对权力— 秩序问题的基本 结论是“相互制衡”。进一步说,从世界各地(尤其是各类“前现代”色彩较浓重的群体)的田野材料来看,对单极强力秩序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普遍现象。格雷伯就此有四点概括:
权力制衡源于一种社会想象,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共识, 而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要不断地“进入他人的视野”来 思考结构何以平衡;
权力制衡是内在于社会的一种权力主导形式,在人类社 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化制度的潜在任务之一就是反对任何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地位差别出现;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如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将源起于将某些特别令人厌恶的支配方式清除出生活;
作为一种想象资源,权力制衡的思想有助于发展新制度、矫正旧制度,在革命时刻人民据此来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形式。
权力制衡源于一种社会想象,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共识, 而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要不断地“进入他人的视野”来 思考结构何以平衡;
权力制衡是内在于社会的一种权力主导形式,在人类社 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化制度的潜在任务之一就是反对任何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地位差别出现;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如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将源起于将某些特别令人厌恶的支配方式清除出生活;
作为一种想象资源,权力制衡的思想有助于发展新制度、矫正旧制度,在革命时刻人民据此来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形式。
所以,如果是对人类学知识有所积累的读者,应该能够在格雷伯看似天马行空的“海盗启蒙主义”推理中读出非常熟悉 的意味。比如格雷伯认为海盗群体因为从事特殊营生,尤其看重“选贤任能”。在执行劫掠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推举最为优秀的行动领袖。任务结束时论功行赏,避免造成内部矛盾。但是一旦任务周期结束,群体回归常态生活,就立即终止该领袖的权力,复归群体内部平等的商议决策。这种弹性的权力分配机 制,广泛存在于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工业化车间生产在内的多种社会形态。我们可以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彻底的“就事论事”,权力的分配和执行,完全取决于群体所面临的任务和状况。
之所以大费笔墨向读者介绍格雷伯思想中的这一底色,主要原因是担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因为缺乏对其分析框架的理解,而误认为他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负责任地说,格雷伯在史料空白处“发挥想象力”的时候,所依托的恰恰是人类学相关领域研究中累积的一般性启示,是一种“人类学的想象力”。
《海盗与启蒙》不是格雷伯第 一本语出惊人的著作。从 《债:第一个5000 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到同样出 版于他去世后的《人类新史》(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格雷伯晚期的一系列著作都曾激起过 对其“研究方法”的激烈讨论。有批评者认为,他为了预先就 已经设定的结论,随意裁剪、筛选材料,以便让论证按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这样的现象对于现代学术体系中 “跨界”参与议题的学者而言并不罕见,表面看是专业壁垒造成的针锋相对,深层原因是论者不理解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人类 学基本观点,不理解当代人类学视野中对类似权力制衡问题的经验累积。
《海盗与启蒙》的英文版出版以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左翼学者诺姆 ·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在和艺术家妮卡 · 杜布罗夫斯基( Nik a Dubrov sky )的一次对谈中提醒我们注意: 我们阅读英国革命的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总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博弈,但是别忘了那个时候民众为了抗争而奔走呼号。人们到处演讲,印刷、出版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希望“被了解人民痛苦的人统治”。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乔姆斯基提醒我们在理 解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不能忘记“社会”,忘记普通人的行动和 见解。
在《海盗与启蒙》的前言部分,格雷伯将这本书定位为自 己多年来一系列专题研究的补充和延伸。我将他这部分努力称之为“启蒙的祛魅”。
自法兰克福学派以降,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启蒙运动及其遗产的反思和批评从未停止,且角度纷呈、洞见迭出。例如启蒙 之暗面、启蒙之暴力、启蒙之口是心非、启蒙之白人男性中心 主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格雷伯的努力,是这一学术传统的延续,但是他独辟蹊径,或可称之为“启蒙之剽窃”。
格雷伯以人类学的独特方式反思“现代性”的努力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早在其有关价值理论的著作中,格雷伯就有意识地与马克思这样的现代社会理论思想家对话。他对话的策略不是在对方所划定的范围内进行逻辑拉锯,相反,他总是立足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经验(尤其是“非西方—非现代”社会的经 验),重新提出问题。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将价值问题的讨论局限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忽视了文明史上“创造价值”乃是人 类社会得以凝聚、巩固、再造的重要手段。运用类似的讨论策 略,格雷伯重新澄清过当代社会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比如生产模式、拜物教等。
从这样的视角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海盗与启蒙》是其早年理论反思路径的拓展和延伸。只不过这一次,“他者”不再是对立经验的提供者,而是概念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格雷伯祛魅启蒙的工作,留下两份比较重要的文本,一份 是《海盗与启蒙》,另一份是《“西方”从未存在过》(“There Never Was a West or, Democracy Emerges from the Spaces in Between ”)。在这两项研究中,格雷伯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了启 蒙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如何源于某种跨文化交流,甚至是非西方 世界思想成果对所谓“西方”世界的灌输。格雷伯颠倒了萨义德东方学的基本框架,将“东方”之于“西方”的必要性从不 对等权力结构之下的异域想象中解放出来。格雷伯认为,相较于工业社会雏形初现的欧洲,广袤的“东方”大地上无疑有更为复杂而多元的思想资源,其中不乏一些激进的社会理念。非西方社会的思想资源,切实滋养过欧洲知识分子,所谓“波斯 人的信札”不是可有可无的弦外之音,而是真正对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成形起到过推动作用的一股力量。
2020 年 9 月,正在与亲友一同度假的格雷伯意外死于坏死性胰腺炎,他针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性工作也因此戛然而止。不过,至少从他留下的这两份文本当中,我们可以习得一种基本 的方法论框架。这一框架是其一生人类学思考的凝结和升华,依然折射出民族志的独特光辉。
坚持以家乡方言(海丰话)创作歌曲的著名摇滚乐队“五条人”,曾经略带戏谑地将自己的创作理念概括为“立足世界,放眼海陆丰”。这个说法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 — 世界” 排序,也开辟出新的阐释空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地方” 和“世界”的关系有着明确的界定。“世界”是“地方”的目 的,是评价“地方”的标准,甚至是“地方”表达自身合法性的唯一参照。彼时国门重开,“世界”的面貌混沌而疏离,但却渗透到各种讨论、分析和对话的字里行间,裹挟着罕见的热忱,成为重新想象自我的纲领。与之相比,“地方”虽然具体、明确甚至亲切,但却没有介入宏大叙事的资格。
“世界”和“地方”之间的不对等想象,可以上溯至近代史屈辱记忆的源头,“世界”随着一声炮响轰然降落,不再是天下模式中无足轻重、聊作谈资的异域。“世界”兼具时空双重意义,既代表着进化序列上的明天,也意味着充斥着陌生经验的强悍异邦。
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层框架,我们常常以为是中性词的“世界”,实则隐含着强烈的价值属性,而这种价值属性的确立,又和我们建基于自身发展迫切要求之上的特定认知框架密切相关。一方面,我们出海远游的目的地非常有限,集中于值得学习的 “列强”;另一方面,在“列强”那里确认的“世界”想象之所以能够成立,前提是对启蒙主义—工业革命所奠基的一套基本概念的接受。这二者常常紧密纠缠、难分彼此,究竟是经验坐实了概念,还是概念的透镜限定了我们所能捕捉到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境中很难说清。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理念、视角和知识取向,与中国人百余年来建设现代学术的规划之间一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张力。人类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一度令知识精英们感到兴奋,但当人类学展开的“世界”画卷中充斥着部落经验、岛屿风俗、小国故事之类的素材的时候,人们又难免怀疑此一 “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当“世界”无法充当我们在救亡竞赛中一个明确的落脚点和补给站的时候,“世界”在空间尺度上的丰富性也就相应失去了价值。
上述考虑,也是我尤为希望向中国读者们推介格雷伯这本《海盗与启蒙》(以及前文所述他“晚年”展开的一系列旨在反 思西方社会基本概念的研究)的原因之一。不妨说得俗一点:格雷伯以民族志特有的策略和方法,证明了人类学为何“有用”,怎样“有用”。这种证明并不诉诸价值观上的选边,而是邀请“世界”加入背书。《海盗与启蒙》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用 “地方”撬动“世界”,这种撬动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澄清。这种澄清既包含对被遮蔽的历史经验的重现,也通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什么才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经验”?
学生时代的格雷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类学训练,跨越重洋,远赴他者的社会展开研究。这本是世界上人类学研究者学术生涯的常规轨迹。但是在必要的田野训练完成之后,终其一生,格雷伯都不只是把“马达加斯加”当作论文材料的来源或学科理论的注脚。相反,身处世纪之交波诡云谲、危机时时浮现的“世界”,格雷伯常常重新返回(抵达?)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所蕴含的思想能量,随着他理论体系的逐渐精进而愈加强烈。立足“世界”,放眼“马达加斯加”,格雷伯既展现了人类学独特的知识抱负配资安全平台,也让看似微观的地方经验有了独特的分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在伦理和价值的意义上,对自己的“田野世界”做出的回馈。
发布于:北京市上一篇:贵金属配资平台 李家超施政报告:北部都会区强力提速,黄金与数字资产抢滩未来
下一篇:没有了
